 刘彦庆
发表时间:2021-12-02 21:13:53
18757
1
11
刘彦庆
发表时间:2021-12-02 21:13:53
18757
1
11
一是脱离自我。任何内在或外在的冲突,要是它的某一方面被压抑住,而另一方面占了优势,那么该项冲突会从知觉中消失而且真正地(人为地)被削减了。从拥有冲突性的需求与利害的两个人或两个团体来看,只要其中一人或一个团体被征服了,那么这种公然的冲突自会消失,在霸权的父亲与被征服的孩子间,不会存有明显的冲突,同样的,对于内在的冲突亦然。我们可能具有一种敌视他人而又需要被人喜爱的明显冲突,但只要我们压制敌意——或压制被喜爱的需求——那么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得简单化一些。同理,如果舍弃真我,那么存于真我与假我间的冲突不会由知觉中消逝,而且由于这种力量分布的巨大差异,这种冲突的确会有所减退。无疑,这种紧张的消除,只有当牺牲自负系统的自主性时方能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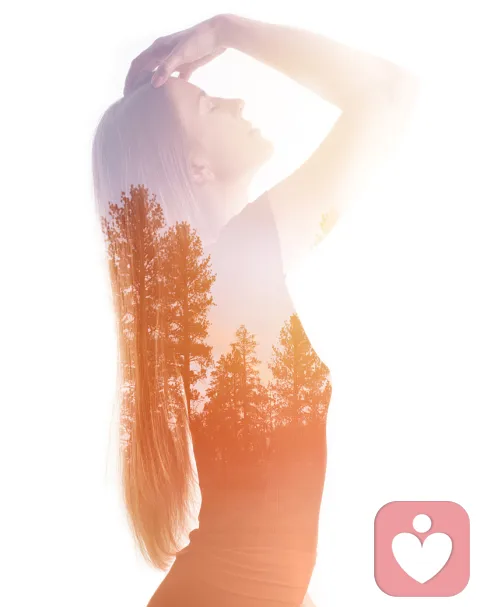
“否认真我”是受自卫利益之指使而发生的,当真我变得更强烈时,我们可以真正地观察到内心激战的狂暴,任何人只要由本身或他人经历过这种激战的凶猛性,都会了解很早便从激战区撤除的真我早已被“求生”的需求以及“不愿被碎裂”的欲望所指挥了。这种自卫的过程,本身主要表现在病人喜欢使问题变得混乱这个现象上,无论从表面上看来他是多么合作,但基本上他仍是个迷惑者。他不只具有使问题变得迷惑的惊人能力,而且不易加以劝阻。这种喜好必定会发生,而且事实上也会发生,其方式就如同骗子在意识层次上所显示的作用一样:情报员必须隐藏他的身份,伪君子必定装出真诚的脸孔,罪犯必定会假造口供。而神经官能症患者,毫无察觉地过着双重生活,同样的,他必定会潜意识地使自己的身份、愿望、感觉与信仰变得模糊不清,而且他的一切自欺行为都是由此而生的。将这种变动明显地归纳为:他不只在智力上对于自由、独立、爱情、善良与力量的意义搞不清楚,而且,只要他不准备与自己发生肉搏战,那么他必具有一个强烈而主观的喜好,以维持这种惶惑——接着,他会利用隐藏在聪慧悟力中的错误自负来掩蔽这种惶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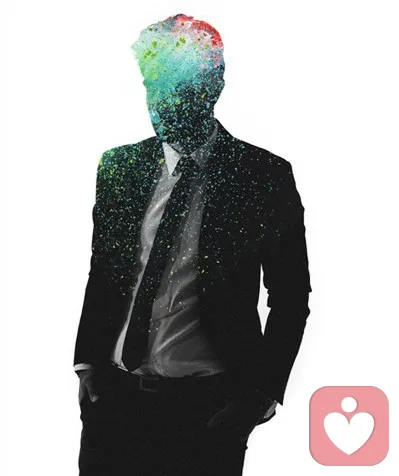
二是内在感受的外移。这并非指心灵内的过程如实地被体验到,而是指体验到了发生在自我与外在世界间的感受,“外移作用”是解除内在系统紧张的根本方法,但它会导致内在的负荷以及增加人际关系的障碍。首先,可以将外移作用描述为一种藉着将所有对不合自己形象的缺点或弊病的谴责,转放到别人身上,来维持自我理想化形象的方法。其次,它是一种否定自毁力的企图,或者是一种掩饰自毁力之间所发生的企图。其内在过程,几乎没有一种不被外移,譬如,神经官能症患者虽然极不可能怜悯自己,但是却会同情他人,虽然他坚决地表示决不渴求内在援助,但他却会竭尽己力地去帮助那些在成长过程中遭受到打击的人。他对内心指使的强制性的反抗,可能会呈现为对传统、法律或势力的蔑视。他不了解自己夸大的自负,在其他方面他可能会憎恨它——或被它所蛊惑。此外,他可能轻视其自负系统的霸权所表现的畏缩,他不知道正在掩饰其自恨的残酷性,他也可能从自恨中除去残酷、严厉甚至于死亡。

三是“认为自己是支离破碎的”这种心理倾向,宛若我们本身就是所有不相干部分的总和。在精神医学文献上称之为“分隔”或“精神碎裂”:他不觉得自己是个完整的有机体,其中每一部分必与整体有关,而且每一部分互相影响、彼此作用。只有被远离和被分裂的人才会缺乏这种整体感。然而,神经官能症患者对于“脱离关系”具有积极的兴趣。如果向他陈述某种关系,他会很聪明地了解它。但对他而言,这只是一种意外罢了,这种洞察力只是肤浅的,随即会消逝的。
例如,在他的潜意识里,对于自己“不了解因果关系”甚感兴趣,就如,某种心理因素由其他因素而产生或者这种因素加强了其他的因素一样,因为某种态度可保护某些重要的错觉,所以需要维持这种态度;大体而论,任何强迫性的倾向会影响他的人际关系或者他的生活,甚至于他无法了解最简单的因果关系。他的不满与要求是相关的,或者他对人们的强烈需求——不管是什么神经官能症的理由——使得他处处依赖别人,这些对他而言都是奇异的。他迟迟不能入睡与其上床时间较晚具有某种关联,但这对他而言就好像是一个惊人的发现。他对于不觉察并存于其身上的矛盾价值,亦具有同等强烈的兴趣。相当真实地,他完全无法了解忍受着甚至珍爱着存在于他自身的两种价值,这两种价值都是自觉的,而且是相互矛盾的。譬如,他将价值放于高尚的品德上,而却又矛盾地将价值建筑在欲使别人对他卑躬屈膝上,或者他希望诚实,但却又心存投机取巧的想法。因此当他尝试反省自我时,也只能得到一个静止的画面而已,仿佛他只看到了拼图玩具中分离的部分一样:胆怯、轻视他人、雄心、被虐待的幻想、被喜爱的需求等等。个别的部分虽然可正确地被了解,但却没有变化,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一种不具任何相干关系、没有过程或者动力变化的感觉。

虽然“精神分裂”本质上是种分裂的过程,但是它的作用在于保存现状,保护神经官能症的平衡以免于崩溃。藉着拒绝被内心的矛盾所困惑,神经官能症患者使自己免于面对根本的冲突,因此他能使内心的紧张维持着低潮,甚至于对那些冲突根本就漠不关心,所以他永远无法知觉到内心的紧张或冲突。当然藉着分离因果关系也可得到相同的结果,剪断因果间的链环,可以使自己免于发觉某些内在力量的强度与关联。举个重要而普遍的例子来说明,某个人有时会深刻地感受到那种报复心魔力的完全震撼力,但他却难以了解受伤的自负与重建自负的需求是这种现象的激发力,而且甚至于当其清晰可见时,其相互关系仍旧会毫无意义。一方面,他可能对于自己的严厉自责有相当清晰的印象,他也许已从多数详细的例子中,了解了这种压服性的自卑,是伴随着他无法符合自负的幻想指使所致,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却会无知觉地破坏了这种关联。因此自负的强度以及自负与自卑间的关系对他来说,充其量仍旧只是一些不明确的推理罢了——这使他不再那么需要去对付自负,这种关联或许还有影响力,但紧张已陷入低潮中了,因为并没有冲突发生,而且他也能够维持一种虚伪的“整合感”。
而有关保存内心安宁的企图,都具有共同的特质,即在于除去足以破坏神经官能症结构的元素:削减真我,排除所有的内在感受,废除那些(要是被了解后)足以破坏平衡的“相互关系”。另一个方法是自主的控制,一部分因相同的倾向而引起的,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抑制情感。在一个面临分裂的精神结构里,情感是危险之源,因为它们仿佛是我们心中难以驾驭的基本力量。要是我们选用这种自制,那么藉此便可抑制出于冲动的一些行为,或突发的愤怒与狂热。无意识的控制,不只用于抑制冲动的表现或情感的抒发,而且在于抑制冲动情感本身,它的作用如同无意识的夜贼与火警,当不想要的情感滋生时,马上可给予紧急的(或是恐惧的)警告信号。但与其他企图相比,这也如其名称所指的那样,是一种控制系统,如果经由脱离自我与精神分裂,而致缺乏一种组织上的统一感,那么需要某些人为的控制系统,以聚合我们自己的每一个矛盾部分。这种自主控制系统可包含所有的冲动及恐惧、受伤、愤怒、愉悦、喜爱与狂热等等情感。广泛的控制系统在身体上的表现有肌肉紧缩、便秘、步伐或姿态的变化、脸部僵硬、呼吸困难等。个人对“控制”本身所表现出的意识反应个个不同,有些人相当敏感而且会为此暴躁易怒,至少有时会失望地希望能够对此释然,能够痛快地大笑,能够喜爱,或者能够深受某些狂热所影响。另外一些人却用有点公然的自负来巩固这种控制,他们将这种自负表现在不同的方面,称这种控制为威严、宁静、禁欲、戴着面具、装出无表情的脸孔,或是“逼真的”、“喜怒不形于色”、“冷若冰霜”。

在其他形态的神经官能症中,这种“控制”所表现的方式具有选择性。于是某些情感会安然地逃脱,甚至于被激励起来,譬如,具有强烈自谦倾向的人,便易于夸大爱情或悲惨的情感,此处的抑制作用最初可根植于敌对的情感内:嫌疑、愤怒、轻视与报复。当然,情感也会由于许多其他因素(如脱离自我、形势险恶的自负、自我挫折),而被加以夸张或压抑住了。然而在无法自制的情况下,“惊醒的控制系统”却会超乎这些因素而起作用,在很多情况下会表现出恐怖的反应——例如恐惧熟睡、恐惧麻醉、恐惧醉酒、恐惧躺在睡椅上自由想象,以及恐惧往下坡滑雪等。贯穿着控制系统的那些情感,不管是怜悯的、恐惧的或凶猛的,都会引起惊慌:这种惊慌可能是因为个人恐惧与推却这些情感所引起的,因为这些情感使得神经官能症的人格结构中某些特有的成分濒于险境,然而也可能只因他了解了其控制系统并未发生作用才会变得惊慌不已,如果对这种情形加以分析,那么恐慌自会消失,同时,特殊的情感以及病人对这种情感的态度也就会变得易于分析。
四是心智的力量。情感——因为难以驾驭——就如该被管制的嫌疑犯一般,而心智——想象与理性——则伸展得有如神话中来自瓶内的精灵一般。于是确确实实地产生了另一种二元论,它不再是心智与情感,而是心智对情感;不是心智与肉体,而是心智对肉体;不再是心智与自我,而是心智对自我。然而,形如其他的分裂作用一样,这也是用以解除紧张,用以隐藏冲突,用以建立“统一”外表的方法。

心智可变为自我的旁观者,就如朱祖凯所说的:“智力毕竟是旁观者,即使它有某些作为,好坏都是个接受吩咐的雇佣。”在神经官能症患者中,心智绝不是个友善的或体贴的旁观者,它多少有些偏私,有些虐待狂,但它永远是超然孤立的——仿佛在注视着一位偶尔与他凑合在一块的陌生人,有时这种对自我的观察显得相当的机械性,且相当肤浅。病人会稍微给予一些有关事件、活动与症状的正确报告,但其增减却未触及这些事件对他所代表的意义,或者他对这些事件的个人反应意义。在分析中,他也可能对于自己的精神过程感到相当有趣,但这种兴趣只是表示他喜悦地观察到隐藏在这种情况之后的狡黠与狡黠技巧,形同一位昆虫学家会被一种昆虫的生理作用所迷惑一样。同样,分析者亦会感到欣慰,而将病人的这种热切的盼望,误以为是病人真正对自己感兴趣。而且不用多久,他就会发觉病人对那些有关其生活的发现所具有的意义毫无兴趣。
这种超然孤立的兴趣,也可能是公然的吹毛求疵、兴高采烈或者是虐待狂的表现。在这些情况下,它通常会以主动的及被动的方式而被外移,他或许仿佛不理睬自己,而万分机敏地以同样超然、无关的方式去观察别人或别人的问题。或者,他将会觉得,他已置身在别人的憎恨及高兴的观察之下——一种在妄想狂情况下所产生的感觉,但这并非只限于妄想症才会发生。不论做个自己的旁观者的性质为何,他已不再参与内心的奋斗与挣扎,他已将自己由内心的问题中移出来。于是“他”变成“观察的心智”,因此他具有了统一感,他的头脑变成自己所能认为唯一活着的部分。心智也像是个协调者,我们对它的作用已很熟悉。我们已经了解了想象的作用,创造理想化的形象,使自负不停地努力以遮掩这个形象,将需求转变为美德,将潜能转变为事实。同样的,理性在合理化的过程中会加强并顺服于自负,于是任何事情变得或被认为是合理的、似真的、正当的——这就像神经官能症患者所依赖的潜意识前提,其所表现的结果一样。

协调作用亦可用以消除任何自我疑惑,格外需要时,则整个构造便越发不稳固。于是有所谓(引用一位病人的话)“盲信的逻辑”,这种逻辑通常伴随着对“绝无谬误”的坚决信仰而产生。我的逻辑占优势,因为它是唯一的逻辑……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人就是白痴,在与他人相处中,这种态度表现出一种傲慢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关于内心的问题,这种表现摒弃了建设性的研究,但同时也藉着建立毫无结果的确实性,从而减轻了紧张的程度,就如同在其他神经官能症的关系中这也是正确的一样,相反的极端——广泛自疑——会导致紧张平静的同一结果。要是每一件事看来都不像是真的,那为什么会有烦恼呢?在很多病人中,这种怀疑论可被隐藏起来,表面上他们似乎很诚心地接受每一件事物,但事实上却将其原封不动地抛在一边,因此他们自己的发现与分析者的暗示就会消失在不可靠的事物中。
最后,心智是个具有魔力的统治者,就如同上帝是万能的一般。虽然对内在问题的认识不再是导致“变化”的步骤,但这种“认识”本身即代表了“变化”,如果病人这么认为而不自知的话,那他们往往会因为任何障碍并未消失而感到困惑,因为病人对于障碍的动力变化过于了解。分析者也许会指出,一定还有许多他们不知道的重要因素(这的确是真的),但是即使病人了解了其他相关因素,事实上,情况仍会是一成不变。于是,病人会感到迷惑与沮丧。因此他们一定会无止境地探求,以便更“进一步认识”自己,这种作法本质上虽有其价值,但只要病人仍坚持不必去做实际行为的改变,“认识”之光应该能消除其生活中的每一疑云时,那么这种“认识自己”的探求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他越用纯智力去处理生活问题,越会无法承认存在于自足的潜意识因素,如果这些因素无可避免地干扰他,那么将引起不成比例的恐惧,或者这些因素就会被加以否定或者被说服,这对于初次发觉本身存有神经官能症冲突的病人而言,尤其重要。他在片刻间便会了解到,即使靠理性或想象的力量,他也无法使矛盾变得和谐,他感到自己掉进了陷阱因而恐惧,于是他会鼓起一切精神力量来避免面对冲突,他如何能规避呢?他如何能躲过呢?他可以从陷阱的哪个漏洞逃出来呢?单纯与奸诈并不会在此共存——喔,那他不能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得单纯,而在其他情况下表现得奸诈吗?或者,要是他被驱使着去报复且以此自傲,探求平静生活的观念也支配了他,那么他会变得被某些意念所迷惑:探求沉着的报复、平静地过活以及希望能消灭阻挠他自负的冒犯者。这种“逃避”的需求等于是他真正所酷爱的东西。一切被用以使冲突明显减除的善良作为,于是变得毫无效用,但内心的“安宁”却因此得以重建。
所有这些方法都以不同的方式减除了内心的紧张,我们可将其统称为“为求解决紧张的企图”,因为在他们当中整合力都在发生着作用。譬如,藉着“分隔”,个人将冲突的倾向解离,因此不再觉得冲突就是冲突。要是一个人觉得他自己是自己的旁观者,那么他会因此而建立起统一感,然而我们却不可能藉着“证明自己是自己的旁观者”而满意地去描述一个人,那样则需要依据他注视自己时所得到的观察,以及他观察自己时的心境而定。同理,“外移作用”的过程也只关系着神经官能症结构的某一部分而已,尽管我们知道他把什么加以外移了或者如何将其外移。换言之,所有这些方法只是部分解决方法而已。这些解决方法也代表了整个心理人格的发展形态与方向,它们还可决定神经官能症患者必须获得哪一类的满足,该逃避那些因素,同时,也可因此而看出患者的价值层系以及他们的人际关系。它们也决定了患者大概使用了哪种整合方法,简言之,它们是生活的方法。
温馨提示:文章、帖子、评语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 给力心理
给力心理







